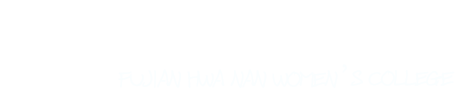1941至1944年,我就读于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。抗日战争时期,学校迁在南平的黄金山上,与南平剑津中学成为邻居。我的两个哥哥:宗汉、宗恒,都在剑津读高中。
最值得纪念的活动是我们两校联合公演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“我站在高山之巅,望黄河滚滚……你是我们民族的摇篮……”
《黄河颂》的男高音独唱者是陈默。
“张老三,我问你,你的家乡在哪里……痛心事,莫提起,家破人亡无消息……”
两个流浪者的《河边对口曲》,由我的二哥宗恒和另一位男生对唱。
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,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……”
《保卫黄河》的男女声大合唱,歌颂了中华英雄儿女抗击日寇,保卫国土的坚强斗志和必胜信心。
高中三年,感谢老师的关怀和教诲,感谢同学的帮助和友爱,我学到了知识,学会了做人。
国文老师沈弢光,培养了我对诗词的欣赏和爱好。我记得他的两句诗:“春雨春风春色新,黄金何处买青春。”诗句一直勉励着我爱惜光阴,力求上进。
数学老师何淑英、戴琼英,训练了我灵活思考,认真运算的能力。
英语老师刘培清,为我打下英语语法的扎实基础。那些不规则动词,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其中的一部分。
我的同窗好友杨耀楣、林曙、郑绿痕、陈淑熙、傅德琼,毕业后曾经联系过,特别是杨耀楣和林曙。我去过耀楣家,她父亲曾在我的纪念册上画过一幅《明月清风》,一轮圆月当空,山崖边几株青松,依稀可见一线清泉流下,可惜后来遗失了。她母亲非常慈祥,能和我话家常,她的哥哥和嫂嫂都极好。林曙较早参加工作,她没有读大学,人是挺能干的,但人生旅途却很坎坷。多年未通音讯,愿她们健康长寿,家庭幸福。
1944至1948年,我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读书。
大学一年级,班主任是仁慈和蔼的王纯懿老师,我和廖翔嫔被指定为正副班长。班上同学人数不少,真可说是来自五湖四海。远的有上海的黄石言、沈明月,广东的戴肇庆、郑启慎,香港的陈桂珍,海外归来的陈嘉庚先生的孙女陈佩贞,近的有南平地区的廖翔嫔、郑丽龄、金能英,古田的钟茂琛、魏纪征、黄声楣、郑启鸿、谢碧杞,福清的施贞和、薛德惠,罗源的黄锦屏、郑美香,莆仙地区的陈如琼、石美爱、黄美英,闽南地区的张仪卿、朱宝安、吴珍芳、陈琼心、周美莲,福州的杨秀钦、陈琼琳、程素琦、郭永华、陈文静、刘贞琼、蒋婉青、李一芳、林金玉、刘以熙,可能还有漏掉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她们的笑容永远年轻。
我们的宿舍在程氏楼三楼,同室三人,杨秀钦、陈如琼和我,都是化学系的。宿舍前有几棵大树,正对着窗口的树上住着一对猫头鹰。它们白天蹲在窝里,一动不动,那脸长得可真像猫,也有耳朵,只是有个尖钩嘴,露着凶相。
杨秀钦高中毕业后先去工作,然后才上大学,因此年龄比我们大些,我们就叫她“钦姐”。陈如琼和我非常要好,有同学取笑说我毕业后会跟她回仙游。
国文老师陈必恒,教我们读屈原的《离骚》,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,至今音犹在耳。
吴芝兰老师教我们《微积分》和《微分方程》,她那端整的板书和专注的讲解,也留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《英语语音学》老师Miss Cole,教我们国际音标,她反反复复地读,我们一遍遍地跟,这使我终身受益。我在福大化学系教化学,也教过英语,还教过教师业余英语班,我准确的读音就是当时打下的基础。
《无机化学》是林升华老师教的,而《分析化学》、《有机化学》、《物理化学》、《生物化学》则都是余宝笙老师教的。她还指导我的毕业论文,翻译一本1948年美国最新出版的《无机化学实验》。她是我的恩师,永远活在我的心里。十年前我写过一册电视文学剧本《八闽女杰余宝笙》,就是对她的深情纪念。
校学生自治会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,如演讲比赛、作文比赛、辩论会,还有以班级为单位的歌唱、舞蹈、球类的比赛,以及上演话剧。我们班人才众多,得了不少奖项,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夺得第一名的《升平舞》。当时二战结束,日本投降,颇有一点“天下太平”的味道。八个人分四对,代表中国、美国、苏联和非洲国家。魏纪征、戴肇庆、李一芳、陈桂珍个头高又漂亮扮男的,程素琦、郭永华、蒋婉青、钟茂琛都是身材娇小的美女,显得十分般配。陈桂珍和钟茂琛扮非洲人,浑身围裹得花花绿绿不说,头上还戴着鲜花和绿叶编成的花环。廖翔嫔和陈佩贞是舞蹈的主持者,廖翔嫔弹着风琴,四对舞者随着琴声踩动舞步,赢得满场最热烈的掌声。
“天下太平”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,内战却爆发了。1946、1947年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,福州“反内战,反饥饿”的呼声也影响到我们学校。当时我正好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,与协和大学、医学院、农学院、福建学院的自治会会长经常在一起开会,还参加了协大学生“反内战,反饥饿”游行。本来我们华南学院的同学也准备参加游行,计划是协大学生游行队伍来仓山和我们会合,大家一早就集合在操场上等待。后来知道他们为了争取时间,已经直接进城了。于是我只好自己一个人乘坐公共汽车去追赶,在洋头口追上队伍,这才随大家一起步行进城,到省政府请愿。
校内上演话剧,我们班也不甘落后。演过一个小喜剧《凤还巢》,我和钟茂琛扮演一对因吵嘴而分居的小夫妻,张仪卿扮演我的岳父。听说岳父大人要来,妻子赶快搬回家,夫妻装着十分亲热的样子,结果还是被岳父痛骂了一通,双方才认了错,重归于好,博得全场笑声阵阵。但更值一提的是我们公演了著名作家曹禺先生的话剧《雷雨》,得到更多人士的好评。
《雷雨》的剧情有点复杂,周朴园老爷年轻时喜欢丫环侍萍,和她生了大少爷周萍,后来在不知侍萍又已怀孕的情况下把她赶走。侍萍投河寻死,被鲁贵救了,就嫁给鲁贵,生下儿子鲁大海。儿子长大了,在周老爷开的工厂里当工人。周老爷娶了太太繁漪,生了二少爷周冲。鲁贵进周家当仆人,他和侍萍的女儿四凤也到周家当丫环,大少爷周萍先和太太繁漪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,又和四凤发生了同样不正当的关系。侍萍想念女儿特地从乡下赶来看她,进了周家才发现这是她三十年前住过的地方。同时周老爷进来认出侍萍,当他良心发现叫周萍下跪认母时,一连串悲剧发生了,周萍回房开枪自杀,四凤在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中冲向后花园,竟触电而死。周冲一直暗恋四凤,他紧随她冲进雷雨中要拉她,也不幸触电而死。侍萍和繁漪双双发疯,周朴园瞬息之间失去所有的亲人,鲁贵也家破人亡。工厂闹罢工,鲁大海站在周朴园的对立面。
《雷雨》的剧情我在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中看到了“翻版”。我觉得这个“翻版”除了极度豪华奢侈和充满血腥味外,实在不怎么样。倒是最后的《菊花诗》,词曲都很优美,别具一格,留下绵绵韵味。
《雷雨》的扮演者列述如下:林金玉演周朴园,她朴实真情,值得深交,后来去了台湾。钟茂琛演侍萍,她多才多艺,与人为善,毕业后回古田教书。廖翔嫔演周萍,她勤勉好学,办事认真,后来去美国工作。我曾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报纸上看到她的照片,足见她有所成就。蒋婉青演四凤,她美丽善良,聪明睿智,大学没毕业就去了美国。沈明月演繁漪,她性情直爽,平易近人,后来回了上海。黄石言演周冲,她严于律己,待人真诚,后来也回上海。周美莲演鲁大海,她胸怀坦荡,乐于助人,后来去了南京。鲁贵则是我演的。
大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欢送毕业班的活动,我们和四年级的姐姐们聚集在一间大教室里开联欢会。节目不多,但很温馨。我们班全体合唱“送别歌”,歌词是我写的:
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
临岐意未阑,
且奏离歌一曲,
祝前程无量,稳渡关山。
南浦晓风寒,
长亭柳色愁看,
望不断天涯芳草,
此去莫相忘。”
毕业班姐姐合唱级歌,歌词是吴毓琛写的,但内容我记不起来了。
我还把姐姐们的名字编成谜语,现在还记得几条:
“群芳竞秀,首选属王者之香。”(谜底:关元兰)
“绿叶婆娑,临风颂虚心君子。”(谜底:吕翠竹)
“金雕玉缕,龙唇凤眼琴。”(谜底:王美瑟)
“异卉奇花,树结长生果。”(谜底:黄嘉种)
“扶桑珍品。”(谜底:王东宝)
“孕育奇珍。”(谜底:吴毓琛)
“璀璨美玉。”(谜底:李丽瑜)
学生自治会还组织公演话剧《水仙花》。有意思的是,它是外国话剧《简爱》的翻版。演员从各班挑选,我扮演男主人公陶先生,有一份偌大的家业,一个可爱的小女儿。欧阳仁扮演女主人公欧阳莹仙,在陶家担任小女孩的家庭教师。吴毓琛扮演陶的疯妻。刘广复扮演疯妻的哥哥,是个律师,他阻拦了陶和欧阳的婚礼。欧阳走了,疯妻突然在家里纵火,陶为救她身受重伤,疯妻葬身火海,房屋财产化为灰烬。
双目失明,贫病交加的陶先生即将走完人生之路,欧阳却奇迹般出现了。她无意中继承了一大笔遗产,为陶先生还清所有债务,决定留下来和他共同生活。这时,年轻潇洒的牧师(由杨碧柳扮演)出场了。他一直追求欧阳,希望她跟他走。而牧师的漂亮表妹(由林甦珍扮演)也出场了,她穿着骑马服,手里挥动着软软的马鞭,冲过来拉着表哥要他跟她走。牧师还在犹豫,但看到欧阳紧傍着陶先生,终于和表妹一同转身离去。
欧阳仁去了国外,她已成为一个作家。吴毓琛去了印尼。林甦珍也在国外。刘广复在师大附中工作,杨碧柳在新华南工作多年,直到去世。
大学四年级,班主任是博学多才的陈叔圭老师,我是班长。陈老师是心理学博士,当时我们面临毕业和毕业后的出路问题,难免有这样、那样的情绪和想法。陈老师正好为我们多方开导解决。由于我父亲在厦门邮局工作,母亲和二哥、妹妹也在厦门,因此1948年我毕业后就去了厦门。我的级友们也各自一方,各有各的工作,各有各的家庭,彼此联系也就少了。
1960年我由厦门大学调到福州大学工作,从福大退休后,来新华南服务五年。1992年因摔伤再次退休。我们在福州的48级友曾经两度聚会,一次是郭永华从广州回来,另一次是程素琦从天津回来。参加的有陈琼琳、杨秀钦、刘贞琼、黄锦屏、黄声楣、施贞和还有我。本来我们同班的陈文静由于休学,1950年才毕业,在医大工作,也已多年未见面了。
几位老友的离去我心中十分难舍。杨秀钦学化学,毕业后改行教数学,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学高级教师,经常担任毕业班的教学和辅导。她记性极好,很重感情,讲解难题既细心又耐心,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都向她请教过几何与代数。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,可以常常见面。后来她生病住院,我只探望过一次就来南京了,不久她就走了。
张仪卿毕业后回漳州工作,她性格沉稳,待人热情,和同班的朱宝安很要好,一直像大姐似的照顾宝安。她有领导才能,社会活动能力强,多年来担任漳州市民盟主委。她还擅长书画和摄影,说她是个完人应该当之无愧,可惜她也离开了。
刘贞琼在师大工作,退休后到新华南。她对级友的情况很是关心。蒋婉青从美国回来,她通知大家去宾馆看婉青。郑丽龄从美国给级友寄来小礼物,也是她一家家去分送。在新华南期间,对我也非常关切。一起吃饭的时候她老给我夹菜,总是叫我多吃点。这么好的像姐姐一样的人竟然说走就走了。
最令我心痛的是郑美香和刘以熙的意外去世。郑美香为人内向,很爱写诗,诗给我看却不让我讲出去。她化学系毕业后又去医学院读医,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。刘以熙为人和善,很爱整洁,平时衣服总是挺的,皮鞋总是亮的。毕业后留在大学里,成为教书育人的教师。两位级友英年早逝,壮志难酬,实在是人生最大的憾事。
话说回来,人生也有很多乐事。1998年,我老伴陈文侃自厦门大学毕业50周年,他们1948级同学一起在厦门聚会,我作为家属一同参加。没想到遇见好友陈如琼,原来她的老伴也是厦大1948级的。我们阔别半个世纪后重逢,真说不出有多高兴。此后我们就靠电话来联系,每逢圣诞节我都祝她快乐平安,健康长寿。她儿孙满堂,已经做曾祖母了。
黄锦屏毕业后一直在师大附中教书,黄声楣和她在一起,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陪文侃去看病,在协和医院门口碰到锦屏和她老伴林民燃。打过招呼后,才知道民燃和文侃是厦大化学系的同学。当时感觉我们这两家关系更加亲近了。锦屏和我同岁,我大她几个月,最近我们通了电话,一起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,我们的心仿佛又变得年轻了。
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。五一节刚过,电波传来广州郭永华的声音,勾起七十年来沉在心底的记忆。她和我从高中到大学同学七年,宿舍的双层床,她睡上铺我睡下铺,她往下一探头,我们就能说上悄悄话。她父亲和我父亲是邮局的同事,也算是世交。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,都喜欢看小说,写文章,背诵古代诗词。她能歌善舞,多次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。她毕业后在广州日报社工作数十年,作为人民喉舌,无冕之王,她是我们班级的骄傲,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尊敬。
该搁笔了,但愿这篇小文章能激起老友们记忆深处的浪花,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,我就非常非常高兴了。
(本文作者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48届校友,福州大学教授)